讲座纪要 | 把穆斯林女性写入东南亚史
“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”系列讲座
从东北亚、内亚到大陆东南亚
(1-9讲分场次纪要)
从列岛、海岛东南亚到印度洋
(1-9讲分场次纪要)
南亚·中亚·西亚青年学者工作坊
(澎湃版、历史系版纪要)
南亚篇(1-5讲纪要)
东南亚篇(1-5讲纪要)
2025年4月18日上午,芭芭拉·沃森·安达娅(Barbara Watson Andaya)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做题为“把穆斯林女性写入东南亚史”的讲座,该讲座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“双一流名家讲坛”暨“强基拔尖人才培养系列讲座”之一,为“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·东南亚篇”第6讲,主持人为陈博翼教授。安达娅教授是世界著名东南亚研究学者,康奈尔大学东南亚史博士、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,专长为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和海上东南亚研究,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(AAS)主席、夏威夷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、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座教授等,著有《其他过去:近代东南亚的妇女、性别和历史》《马来西亚史》等,参与撰写《剑桥东南亚史》及主持新的修订版,2000年获得古根海姆奖。

安达娅教授以东南亚史学研究中的性别视角缺失为切入点,开启了一场关于穆斯林女性历史叙事的深度探讨。她指出,在1400至1800年的前近代历史书写中,女性角色与母系亲属关系长期被边缘化,这一现象在东南亚尤为显著。尽管该地区以文化多元性和宗教交融闻名,但穆斯林女性的历史经验却鲜少被系统探讨。这一学术空白不仅源于史料的匮乏——尤其是前近代时期的文献——更受到传统史学中男性精英视角的主导。安达娅教授强调,重新审视这些被遮蔽的叙事,不仅能够补全地方史拼图,更能揭示性别权力与全球性议题(如殖民扩张、宗教传播)之间的深层互动。
讲座伊始,安达娅教授以一则流传千年的传说为引,揭示了历史书写的复杂性。11世纪爪哇传奇女性“Maimun之女”在《巽他史记》中被记载为“前往满者伯夷传教的伊斯兰公主”,其墓碑铭文刻有“Binti Maimun”(Maimun之女)字样。然而,这一简单记载在20世纪初被殖民学者重构为“殉道者法蒂玛”,赋予其宗教牺牲的悲情色彩;2004年,法国学者卡卢斯(Kalus)和吉约(Guillot)却试图颠覆了这一叙事——他们认为,这块石碑实为15世纪从地中海运抵爪哇的船锚部件,与当地伊斯兰化进程并无直接关联。耐人寻味的是,印尼地方史教科书(如胡斯努尔·哈基姆2022年著作《完整的爪哇伊斯兰史》)仍将其作为既定史实。安达娅教授指出,这一案例暴露了历史书写中“事实”与“虚构”的永恒张力:地方社群通过重构传说满足身份认同需求,而学者则需在批判性解读与尊重文化传统之间寻求平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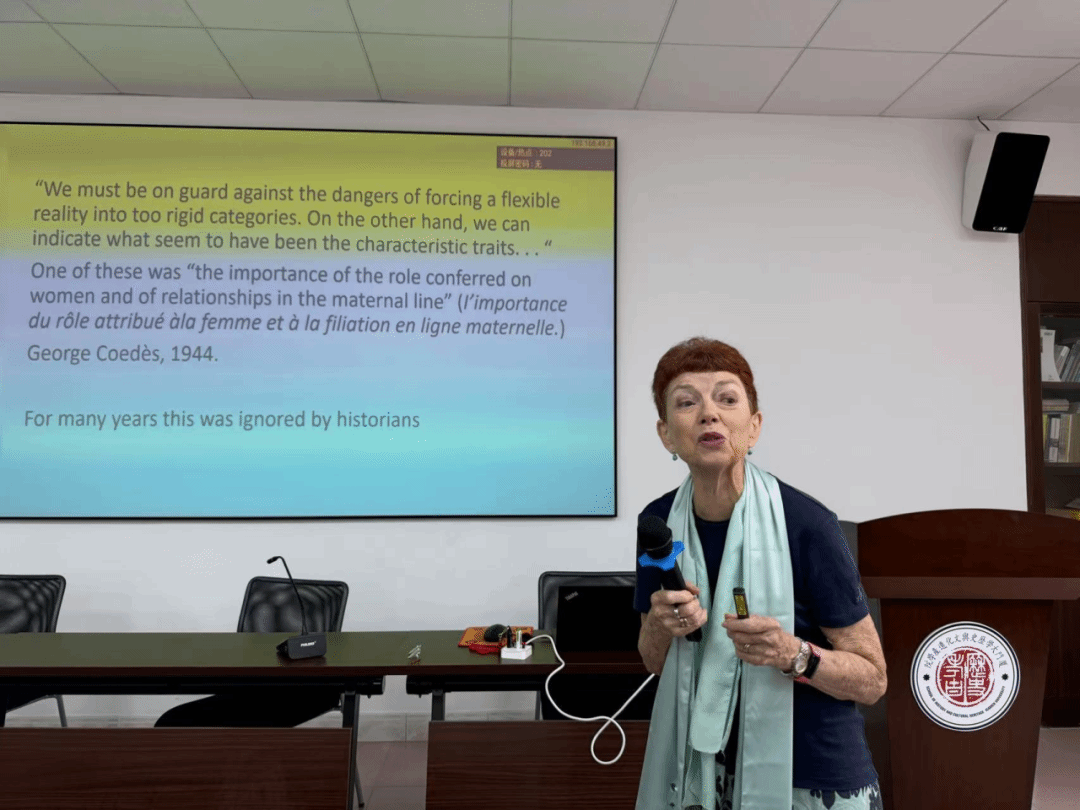
从传说的迷雾中抽身,安达娅教授将目光转向物质文化的变迁。她以“猪的消失”为隐喻,剖析伊斯兰化对东南亚社会的双向塑造。前伊斯兰时期的爪哇,猪不仅是重要家畜——考古发现大量满者伯夷时期的猪型存钱罐,更承担着仪式功能。1511年葡萄牙探险家皮列士(Tomé Pires)曾记载:“全岛到处都是猪。”然而,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,猪逐渐退出公共领域。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:19世纪荷兰殖民档案显示,民间仍存在养猪的现象,暗示着文化转型的复杂性与地方实践的韧性。
宗教对性别规范的重构,成为讲座的核心议题之一。安达娅教授对比了不同时空中的女性境遇: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,穆斯林女性骁勇善战的形象被殖民者刻意塑造成戏剧中的“反派”,以此强化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二元对立;而在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王国,法国传教士尼古拉斯·热尔韦(Nicolas Gervaise)根据流亡王子的口述,写下“女性婚后即沦为奴隶”的论断,却与当地女性以毒药惩处不忠情人的民间传说形成鲜明反差。这种矛盾在棉兰老岛更为显著——17世纪英国旅行家记载“穆斯林贵族女性深居简出”,而百年后的另一位观察者却惊叹她们“外出自由堪比欧洲女性”。安达娅教授指出,这些碎片化记录警示我们:伊斯兰教法对性别角色的规训始终与地方文化博弈,女性既可能成为教义渗透的载体,也可能化身为抵抗的符号。
这种抵抗在宗教实践中尤为隐秘而深刻。即便在男性书写的宗教文本中,女性亦能找到协商空间——17世纪布吉斯与望加锡的伊斯兰手册详细规定交合时机与祈祷文,却暗示妻子可通过遵循教义获得生育主动权。安达娅教授以法蒂玛(先知穆罕默德之女)的形象流变为例,展现女性如何将宗教符号转化为生存策略。在分娩仪式中,马来妇女将写有经文的护身符“塞鲁苏·法蒂玛”(Selusuh Fatimah)系于右臂,祈求法蒂玛赐予平安;而传统助产士使用的Kacip Fatimah则是一味药材。法蒂玛之名可被用于多种场景,亦可用来约束拈花惹草的丈夫,时至今日也是如此。
苏菲主义(伊斯兰神秘主义)为女性提供了另一条突破路径。安达娅教授援引13世纪学者伊本·阿拉比(Ibn Arabi)的理论,指出其将女性视为“神性启示的媒介”,认为“对安拉最完美的冥想需通过女性实现”。这一思想在东南亚化为具体实践:苏菲文本以纺织、蜡染等女性劳动为灵性隐喻,将织布机比作宇宙秩序,染色过程象征灵魂净化。18世纪爪哇的康吉恩·拉图·卡迪帕滕(Kangjeng Ratu Kadipaten)正是借此跻身宗教权力网络——作为沙塔里教团弟子,她将苏菲思想传授给孙子佩多诺罗二世(Pangeran Diponegoro),间接推动了1825—1830年的反殖民战争。安达娅教授强调,此类案例颠覆了“女性仅能依附男性宗教权威”的刻板印象,她们往往通过家庭纽带与劳动技艺,悄然重塑宗教话语的结构。
政治领域的女性权力则更为显性而脆弱。安达娅教授以亚齐苏丹娜塔贾尔阿拉姆·萨菲亚图丁·沙(Sultanah Taj al-’Alam Safiyyat al-Din Syah)为例,剖析女性统治者的合法性建构策略。这位苏丹娜在丈夫去世后一位严厉却慈爱的母亲形象的掌权。爪哇的拉图·帕库布沃诺(约1657—1732)委托编纂苏菲文本,宣称“先知三大挚爱(礼拜、香料、女性)中女性为首”,并自诩“爪哇万民的护身符”。然而,女性统治终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父权体系:1699年,亚齐以“麦加教令禁止女性执政”为由终结女性苏丹时代。
讲座尾声,安达娅教授将焦点转向口述传统的历史价值。她以马来传说中的西蒂·旺·肯邦(Siti Wan Kembang)为例:这位“女王”的存在从未被考古证实,却在吉兰丹、北大年等地的口述史中成为马来民族主义的象征。安达娅教授认为,这一案例表明了口述传统的创造力,也揭示了当地社群渴望将女性纳入历史叙事的愿望,历史学家必须以敬畏之心对待这些传说。
在最后的反思中,安达娅教授坦言,重构东南亚穆斯林女性历史注定是一场未竟之旅。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知识储备是不平衡的,且概括性结论先于案例研究的基础构建是不足的。我们需要更多的案例研究、更多的合作,以及对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源的更多数字化。我们在理解东南亚穆斯林女性历史上已取得长足进展,然而我们的知识永远只能是部分的,通往过去的门扉永远不会完全敞开。
厦门大学施雪琴教授、陈遥副教授、陈瑶副教授、沈惠芬副教授、张淼副教授、黄肖昱博士、娄湘旖博士等出席并与安达娅教授进行了热烈讨论。讲座尾声,陈博翼教授结合当前学界热点和自身经历,对本场讲座概括总结并分享了心得体会。提问环节同学们积极踊跃,安达娅教授一一做了详尽的解答。最后,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安达娅教授的感谢,本场讲座圆满结束。
文:周逸驰
图:陈博翼
排版:陈星宇
责编:赖欣
审核:陈博翼